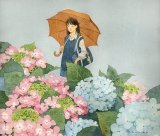摘要: 原標題:為什么今天我們更加需要魯迅? 《魯迅》 如果現代文學的名人堂只有一個席位,那么入選的作家毫無疑問是魯迅。 盡管他在生前身后都不乏爭議
原標題:為什么今天我們更加需要魯迅?
《魯迅》
如果現代文學的名人堂只有一個席位,那么入選的作家毫無疑問是魯迅。

盡管他在生前身后都不乏爭議,但若論創造力、思想性和國民度,目前還沒有哪個現代作家可以和魯迅比肩。魯迅和魯迅文學具有一種獨特的魅力,魯迅的思維方式和表達方式也是他留下的、最為重要的精神遺產。
在本期節目中,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講師李浴洋對話北京大學中文系資深教授、中國魯迅研究會理事錢理群,探究魯迅和魯迅文學及其對現代社會的重要影響。
來源| 看理想節目《文學的現代中國:1635-2066》
對談人| 李浴洋、錢理群
1.
從邊緣到中心的中國觀察
李浴洋:您今年已經85歲了,您和魯迅相伴已經有將近70年的時間。我想知道在這漫長的時間中,您對于魯迅的閱讀、接受或闡發,大概分為幾個階段?
錢理群:我真正認真閱讀魯迅,是在中學階段(雖然最早的接觸是在小學),主要是讀魯迅小說和散文,和戲劇家曹禺、詩人艾青一起,并列為我最喜歡的三大“現代文學家”。
因此我對魯迅的認識是從“文學家的魯迅”入手,而且當時并沒有把他放在特殊地位。這是中學階段的魯迅觀。
1956年上大學,同年出版了《魯迅全集》,我就從有限的生活費中擠出錢來購買了這套新出版的《魯迅全集》,開始全面、系統地閱讀魯迅作品。
1960年大學畢業,我去往貴州安順衛生學校任語文教員。當時我做了兩個選擇:首先是定下了“當最受學生歡迎的老師”的現實目標,同時,又立下“研究魯迅,回到北大講魯迅”的理想目標。所以我對魯迅真正的研究和對魯迅精神的關注和把握,是在我到貴州以后。
畢業后我回到北大讀研究生,1981年研究生畢業留校后,我在北大整整講了21年的魯迅。又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開始了獨立的魯迅研究。
李浴洋:您曾經概括過,大概以21世紀即您退休前后為界,此前的1980到1990年代,您主要是一個魯迅的研究者。
而到了2000年以后,確切的說從90年代后期開始,您就轉向以魯迅為資源,進行各種各樣的文化和社會實踐,用您自己的話說,就是要“接著魯迅往下講,往下做”,這一點能具體解釋一下嗎?
錢理群:這首先是基于我對魯迅思想的實踐性、當代性的認識。研究魯迅如果脫離了我們所處的時代和當下的現實世界,那么跟魯迅是隔的。 我認為魯迅是具有當代性的,而且有很大的實踐性,或者說我是用魯迅的方式,和當代青年發生一種內在的聯系。
我做這樣的選擇,也有一個自我反省。我和我們這一代人,是在“批判封(封建主義)、資(資本主義)、修(修正主義),與傳統文化、世界文明徹底決裂”文化背景下成長起來的一代知識分子。
我又沒有進行后天彌補,就形成了先天的知識結構的缺陷:第一是不懂外文,第二是古代文化修養嚴重不足。這樣我就成了一個“沒有文化的學者,沒有趣味的文人”。
這樣的“研究者”,是很難真正進入魯迅的內心世界的——因為魯迅是學貫古今中外,有著濃厚的文人趣味的。我缺少這兩者,研究到一定程度就深入不下去了,這是我把研究重心轉移到實踐方面的最根本的原因。
到了新世紀,我積極投入了中小學語文教育改革、青年志愿者上山下鄉運動、民間維權運動和政治體制改革運動等社會實踐中,最大限度地利用了魯迅的資源。
我之所以后來在青年中影響越來越大,跟這些是有關系的——是魯迅把我和當代青年、和當代現實緊密地聯系在了一起。
《覺醒人生》
李浴洋:我們知道一個非常有名的故事,1978年您考取北大中文系的第一屆研究生時,是帶著一部30萬字的魯迅研究的書稿前來考試的。那么現在回過頭看,貴州和北大這兩個精神基地,究竟在您的生命史上發揮了怎樣的作用?
錢理群:當年我離開了貴州,到了北大,但我沒有忘記貴州的這些資源。而且把貴州的資源和北大的資源結合起來。
這實際上是創造了一種觀察中國的方法:在中心到邊緣、精英到平民之間,自由地流動,來觀察中國。所以我覺得我對魯迅的理解和對中國的理解有許多獨到之處,這很大程度上依靠了我在貴州和北大之間流動的經驗。
這樣一種從內部,而且是從底層到中層到上層的觀察中國的方法,我覺得在當下都還是非常有意義和價值的。
2.
今日大變革的核心是解中國之謎
李浴洋:在我看來,所謂“錢理群魯迅”,即錢老師對于魯迅資源的獨特運用,其中最大的特色是實踐性,或者說把魯迅轉化成了行動的力量。
今天,我們已經進入了移動互聯網時代,我們獲取古今中外各種思想資源的便利性和選擇性都會大很多。那么在您看來,和其他各種各樣的資源相比,魯迅對于今天的獨特啟示和價值是什么?
錢理群:研究界有一條重要的史料發現:1930年代日本學界在翻譯、介紹《大魯迅全集》時,對魯迅作出了兩個重要評價。
第一,要解“中國之謎”,必須讀《魯迅全集》。第二,魯迅對“中國之謎”的解讀,不止從純文學的角度,而是涵蓋了政治、經濟、思想、文化、人文學角度。這兩點對今天都有很大的啟發性。
今天的中國世界正面臨“歷史大變革”,這一“歷史大變革”核心的問題就是如何認識現當代的中國,也就是如何解讀“中國之謎”。在我看來,現代“中國之謎”已經成為當代的民眾、知識分子,也是當代的青年,最感到困惑的。
魯迅怎么解“中國之謎”?根據我的研究,他有四個方面的反思:反思以儒家的現實主義為中心的中國傳統文化;反思中國的皇權體制;反思中國的國民性;反思中國的知識分子。 魯迅這四大范式依然是我們今天求解“中國之謎”的很好的切入口、突破口。
還有一點,解“中國之謎”不僅是中國的民眾、知識分子、青年最感困惑的問題,同時也是世界中國學的核心問題。所以我反而覺得,現在更加需要魯迅了。
李浴洋:我知道您近年來也在關注中國的國民性,進行相關研究。您可否和我們分享一下您在這方面的最新思考?
錢理群:我有一個思考:大陸的中國國民性和海外的中國國民性好像不完全一樣。那么大陸的中國國民性有什么問題?這是我思考的中心。
這里可以解釋一個現象:我寫的這么多文字,實際產生影響的是一句話,“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很多人知道有錢理群就是因為這句話;很多朋友對我說,“錢理群,你寫這幾百萬到千萬字的文章,最后還比不上你這一句話”。
我現在明白了為什么我這句話會產生如此大的影響。 “精致的利己主義者”正是當代國民性的核心問題。當代很多問題都是出于這種“精致的利己主義”的選擇,在這方面有很大的研究余地。
《覺醒人生》
李浴洋:我注意到您經常把魯迅和周作人并舉,特別是最近幾年,您提倡要做周氏兄弟的綜合研究。您不僅在研究中長期關注魯迅,也寫下了《周作人傳》《周作人論》這樣一些開創性的著作。
您為什么特別強調把魯迅和周作人放到一起討論?引入周作人,對于我們理解魯迅有什么幫助?反之,以魯迅為參照,我們又能照出周作人的哪些遺憾和經驗呢。
錢理群:我先概括一下學術界對魯迅、周作人的認識評價,基本有兩個層面。
一是強調周氏兄弟思想根底上的一致性:都以“立人思想”為基本關注與追求,始終堅守“人的個體精神自由”。在我看來,這也是“五四”開啟的中國現代啟蒙主義的基本命題,周氏兄弟的巨大影響力也是由此而產生的。
但同時,學術界也幾乎一致地指出他們之間有著巨大的差異和分歧,主要是他們對現實生活的態度、行為方式、歷史決策的選擇不同,特別是面對民族意識、民族危機的時候。周作人政治上的失誤導致了魯迅和周作人的分道揚鑣。
在此基礎上,我又有新的深入,我更關注把他們看作一種有意味的參照,他們更深層面生命形態選擇的差異、矛盾、困惑,超越了民族、國家、時代,顯示了人天性中的悖論。
我由“魯迅——周作人”自然聯想起屠格涅夫筆下的“堂吉訶德——哈姆雷特”兩個典型。堂吉訶德—哈姆雷特是世界型的人性的兩端,“魯迅——周作人”也是超越了具體國家民族而具有人的本性的方面。
因此我認為魯迅—周作人體現著“人類天性中兩個根本對立性特征”,都是“人性的旋轉之軸的兩極”。也就是“生命之重”與“生命之輕”這樣的生命形態(心理,情感)的兩極選擇的張力中搖擺。
李浴洋:在周氏兄弟之間,您的選擇是否也有某種傾向性?
錢理群:這是很明顯的:我更多地受到魯迅的影響。這自然有深刻的時代背景與個性原因。
在我看來,魯迅是一個“動蕩不安”的年代里的“精神界戰士”,是一種強者的選擇,追求的是“非常人生”。周作人所作的是一個“凡人的選擇”,追求“尋常人生”,他更適應于“和諧發展”的時代。
而我一生也都是在動蕩不安的年代中度過,我內在的浪漫主義、英雄主義的精神氣質,決定了我選擇了魯迅式的“學者兼精神界戰士”的道路,自覺追求“非常人生”。
但我內心深處,卻又充滿了對“個體的,審美人生”的向往,隨著年齡的增長,就會發生人生選擇上的微妙變化。特別是到了老年,我就逐漸自自然然地對“尋常人生”的“凡人選擇”產生濃厚興趣。
這些年,我經常掛在口頭的“人與自然的和諧”、“人的日常生活”、“閑暇人生”這些話題,其實都是周作人的命題,我自己的學術研究也就轉向了養老學、幼兒學、未來學,倡導回歸“生命的本真狀態”。
我也因此加深了對周作人思想的認識:他倡導的“生活的藝術”,是建立在現代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基礎之上,是一種“生活的現代化要求”,具有“未來因素”。
當然,魯迅的影響也依然存在。可以說,到了晚年,周氏兄弟的影響就逐漸在我身上融為一體了。
3.
最后一個知識分子
李浴洋:我們講了那么多魯迅的意義、魯迅的價值,但在我們充分肯定他的同時,究竟應當怎樣看待魯迅的不足?
錢理群:我提出了一個新命題。我對魯迅有一個判斷:魯迅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最后一個知識分子”。
首先,魯迅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質疑者、批判者,他的廣度和深度在現代中國是無可比擬的。第二,魯迅更是中國文化優秀傳統的傳承人——他不僅是反叛者、質疑者,同時又是繼承人。第三,魯迅也留下了他沒有解決的問題。我不準備簡單地用“魯迅的不足”來概括,這是由魯迅思想特點決定的。
魯迅思想的一大特點是“反烏托邦性”,他著力于引導世人“正視淋漓的鮮血”,著眼于“現實”的存在,而將“未來”懸置。你看魯迅作品,從來看不到他談未來,他是有意地把未來懸置起來了。這是和周作人很大的不同。
我們都被魯迅的不屈不撓所感動,但我研究魯迅越深入,越覺得我很難做到他這樣。我就想魯迅為什么能夠不屈不撓地反抗,我的研究結果是, 魯迅是仰仗著他個人的超強的意志力。
所以尼采對魯迅的影響是帶有更根本性的,他具有一種超強的個人意志力,因此他能扛住,不屈不撓。而這樣的超強意志力,一般人做不到。
魯迅依靠超強意志力,他同時就不會寄托于彼岸的關懷和信仰。這是和我的精神氣質有差別的:我是一個絕對的理想主義者,有彼岸的關懷。
而這樣的彼岸關懷與信仰的缺失,又恰恰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不足。所以魯迅沒有解決的問題,就是沒有解決中國傳統文化中缺少彼岸關懷和彼岸信仰的根本性的弱點。
所以今天我不談魯迅的不足,而是看魯迅的不足背后反應出的傳統文化的不足。這是我的新解釋。
《覺醒人生》
李浴洋:非常感謝錢老師今天來到我們的節目,和我們分享您的魯迅觀。其實您的魯迅觀的背后是您的文學觀、人生觀。
我們知道您是幾代青年的好朋友。您今年85歲,而我們的聽眾可能是25歲、35歲或45歲。那么,您有沒有什么想和大家說的、提醒的,或者交代的話呢?
錢理群:2008年汶川地震時,我已經意識到世界發生了巨變。當時我就跟年輕人提出一個問題:你們的年齡距離我的年齡有40、50甚至60年,這些年是屬于你們的。在你們面對這幾十年的歷史巨變時,你們會遇到些什么問題?哪些是我們這一代沒有遇到的問題?你們準備好了嗎?
今天,我在和年輕一代告別的時候,我是自覺地要退出歷史舞臺了。我也想問這個問題:你們對屬于你們的、未來的40、50、60年的中國和世界的變化,有沒有好奇心?有沒有想象力?對這樣一個變化,你們準備好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