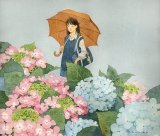摘要: 原標題:清華大學夏瑩:用哲學的眼光,與時代和生活對話 夏瑩,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長聘教授,博士生導師,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日新書院副
原標題:清華大學夏瑩:用哲學的眼光,與時代和生活對話
夏瑩,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長聘教授,博士生導師,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日新書院副院長

夏瑩和哲學的緣分始于1994年。彼時的高中生夏瑩剛拿到保送名額,出于對未知的好奇和浪漫情懷,她在歷史和哲學之間選擇了哲學。
但入學之后,夏瑩一度不好意思說自己是學哲學的。因為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中,哲學似乎與日常生活相距甚遠,被認為抽象而不實用。當人們習慣性地為學習非實用學科的人惋惜時,夏瑩自報家門的聲量和自信也隨之被壓低。
真正和哲學建立無法割舍的關系,已經是博士階段的事情了。在此之前,夏瑩一直夢想著成為一名記者。在碩士研究生時期,她曾到媒體實習,甚至扛過攝像機下一線拍攝紀錄片。“每次談論一些選題,都會說我的角度很獨特,問我從哪想出來的。我當時想這在哲學里是很正常的思維,所以覺得也許我再讀一讀哲學,再從事新聞的話可能會更有意思一點,于是就考了博士。”
以哲學為志業
2001年,在山東大學取得學士和碩士學位后,夏瑩考入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攻讀哲學博士學位。撰寫博士論文期間,她沿著西方馬克思主義方向繼續拓展,遇見了鮑德里亞的《消費社會》。鮑德里亞認為,貨架的擺放、物品的排列都會影響人們的購物行為,而在消費社會中,每件物品都不僅僅是它本身,還象征著社會地位、身份和價值。簡而言之,現代社會已經不再單純以生產來定義人,而是通過消費來標識個體在社會中的位置。
鮑德里亞帶夏瑩看到了截然不同的哲學。原來所有看似抽象的命題和概念背后,都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
夏瑩突然想到了自己的父親,夏老先生是一個會計,每次看到報表嘴角都會不自覺上揚,因為在他看來,報表是那么規整,那么美。正如父親在報表中讀出邏輯和秩序的樂趣,夏瑩也在哲學中逐漸感受到其獨特的趣味,覺得天底下沒有比這個再有意思的學問了。
在學術靈韻的感召下,夏瑩最終完成并出版了自己的博士論文《消費社會理論及其方法論導論:基于早期鮑德里亞的一種批判理論建構》,自此踏上學術之路。
從清華大學畢業后,夏瑩進入南開大學哲學院任教,逐漸展露學術鋒芒。2008年,她翻譯出版了鮑德里亞的《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并因此獲得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頒發的“第九屆(2009年度)引進版優秀圖書獎”的社科類優秀獎。同年,她受聘為復旦大學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之后前往巴黎索邦第一大學訪學一年。
2011年9月,從清華大學畢業六年后,夏瑩調入清華大學哲學系任教,至今已有十三年。
讓馬克思年輕化
在夏瑩的學術研究中,讓馬克思的思想“年輕化”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世人眼中的馬克思是嚴肅而遙遠的,留著大胡子、睿智而高深莫測,似乎高高掛在理論的殿堂之上。他是《資本論》的作者,是共產主義運動的思想奠基人,是一種符號性的人物,象征著革命、階級斗爭和深刻的社會批判。
夏瑩眼中的馬克思則生動而富有活力。“濃眉大眼、青春洋溢、英俊、睿智,他的眼神一定是很深邃和堅毅的,有一種不服輸的倔強的感覺。”她認為,馬克思并非冷峻的“經典”,而是一個以生命體驗探索現代社會的“現代性批判大師”。
2018年,馬克思誕辰200周年之際,夏瑩“趣讀馬克思”系列的第一部專著《青年馬克思是怎樣煉成的?》于人民出版社出版。夏瑩以生動的文字講述了馬克思從青年時代到思想成熟的過程,向讀者展示了一個有血有肉的馬克思。在她的筆下,青年馬克思充滿了對時代的緊密關切,他不僅批判性地思考社會,還洞察到現代性帶來的加速變化。目前,“趣讀馬克思”系列的第二部《為什么出發?:馬克思和他的時代》也已出版,第三部《資本變形記》也即將付梓。
夏瑩相信,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和現代性問題的洞見在當今社會依然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她提到,馬克思的經典名句“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不僅是對資本主義社會的詩意批判,還揭示了現代消費主義中人和物關系的速朽性。現代人對消費品的快速替換、對情感依賴的淡化,都是這種速朽性的具體表現。
在西方馬克思主義和當代法國哲學領域深耕多年后,2019年,她獲評教育部青年長江學者;2022年,她入選教育部長江特聘教授。這一系列榮譽不僅是對她學術成就的肯定,也標志著她在哲學研究領域的影響力正逐步提升。
從傳統哲學到未來哲學
“貓頭鷹只在黃昏起飛”,在傳統哲學的框架內,哲學是一個封閉的體系,它當像夕陽西下時的思索,在一個事情的終結處起飛,遙望并總結過去。傳統哲學家也總是給人高高在上的陌生感。古希臘喜劇劇作家阿里斯托芬在他的著名劇作《云》中設計了一段哲學家蘇格拉底坐在空中吊籃上與主人公對話的場景,具象地體現了人們眼中哲學家脫離人間煙火的形象。
阿里斯托芬
但未來哲學并非如此,它是“高盧雄雞”式的哲學,像雄雞高唱著迎接黎明一般,以開創性、高昂的姿態指向尚未發生的未來。
邁入二十一世紀,人類面臨著一種全新的生存境遇,而哲學也逐漸逼近理論瓶頸。夏瑩認為,傳統哲學在近代逐漸演變成了一個缺乏身體性、僅存頭腦思維的體系。自笛卡爾提出“我思故我在”以來,哲學的重心從身體移向了純粹的思維活動,忽視了人類對痛苦、愉悅、觸感的直接感知。這種“只有頭顱”的哲學模式使哲學脫離了現實生活,逐漸變得抽象而疏離。
笛卡爾
夏瑩開始反思:“如果哲學繼續以抽象的概念所構筑的封閉體系的方式展開自身,每個人背熟了體系就似乎掌握了它的話,哲學的生命力將被全部扼殺。”她相信,真正的哲學不僅要有頭腦,更要有“身體”——一個能感知、回應并反思生活的身體。
為了破局,同時給當代人的生存一個新的可能性,夏瑩認為應用“未來哲學”打碎傳統哲學的封閉性和規定性。德國哲學家費爾巴哈在《未來哲學原理》中說道:“未來哲學應有的任務,就是將哲學從‘僵死的精神’境界重新引導到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精神境界,使它從美滿的神圣的虛幻的精神樂園下降到多災多難的現實人間。”
“未來哲學的關鍵在于觸動,而非闡釋、傳達、講授。真正核心的只有一句話,‘是否真正地觸及到了你’。”如果說傳統哲學是旁觀的哲學,未來哲學就是行動的哲學。夏瑩提倡將身體的觸感重新納入哲學,使哲學不再是抽象的思辨,而是“具身化”的、可以被感知的存在。
在有關未來哲學的探索中,夏瑩對“啪嗒學(Pataphysics)”情有獨鐘。法國戲劇理論家阿爾弗雷德·雅里,于1898年借著浮士德若爾博士之口宣布了“啪嗒形而上學” 的建立。所謂“啪嗒”指的是哲學思維中瞬間的頓悟時刻,使人從既定框架中驚醒,觸及新的可能性。這種瞬間覺知不僅是思維的活動,更是與生活和感知密切相連的觸感體驗。而在劇場空間上演的戲劇,恰恰具備了給人“啪嗒”一下的功能。
去年,夏瑩將哲學引入劇場,以“一折戲劇——思想的精靈在劇場游蕩”為主題,舉辦了清華第一屆“哲學-戲劇節”。
戲劇是“有身體的語言”,是讓人們在現實空間中相遇、感受彼此的存在。“你有一個頭顱不能叫有生命,僅有身體也不行,必須將兩者結合起來。也就是我們不僅有真實的痛,有真實的感觸力,我們還要把這個痛和感觸以反思的方式重新思考:我們為什么在痛?我們為什么會有這樣一種感觸?我們感到的疼痛、愉悅、冷熱,這些東西是為了什么?是因為什么而起的?”通過戲劇,我們得以重新感知自我、反思生活,并借此找到新的可能性,為當代人的生存提供一個更具活力的答案。
生動活潑的哲學教育
在清華,夏瑩開設的基本都是與哲學學科有關的傳統人文類基礎課程,例如《西方馬克思主義》。
作為新一代的哲學教師,夏瑩在教學中強調讓哲學“活起來”,通過問題導向和對現代生活的關切,讓學生們理解哲學的現實意義。“我們主要的工作是引導學生在概念和命題背后探尋它們的現實基礎,幫助他們理解這些哲學概念是如何從生活和時代中產生的,并且要在生活、時代和思想之間建立一種對話關系,形成有意義的連接,使學生能夠看到哲學與現實的緊密關聯。”
有別于許多人的刻板印象,夏瑩的哲學課堂是非常輕松的。一位學生曾在課后對她說:“老師,您的課講得不錯,但我有點困惑,感覺哪里不太對。”夏瑩問他怎么不對,他回答道:“我覺得上哲學課應該是非常努力的,攥著拳頭,全神貫注,帶著一種沉重甚至疲憊的感覺。但是在您的課上,我居然會忍不住笑。這種笑是一種會心的笑,好像戳中了我,帶來一種精神上的愉悅和忽然疏解的輕松。我有些疑惑,這樣的感覺是不是不太對?”
夏瑩笑著搖頭,告訴這個學生,這恰恰是把握到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表現,并將這種困惑和愉悅當作對她教學最大的褒獎:“這種感覺也許是哲學未來的形態應該有的,或者是我們應該努力創造新的哲學形態,這是第一步。”
憑借著獨特的教學方式,夏瑩于2016年被評選為“清華大學畢業生心目中的好老師”,并榮獲清華大學年度教學優秀獎。她的線上課程《馬克思與當代歐陸思想》獲得國家級一流本科課程。
2021年,清華哲學系入選教育部基礎學科拔尖學生培養計劃2.0基地,人文學院哲學系也隨之成立哲學學堂班,成為了清華學堂人才培養計劃項目一員,夏瑩被任命為哲學學堂班項目主任。
哲學學堂班的培養計劃為學生提供了更多定制化課程,在側重經典文獻的閱讀和研討的基礎之上,嘗試建設更富有探索性的課程主題。例如與北京大學藝術學院聯合開設的哲學與電影,與清華藝教中心聯合開設的哲學與戲劇以及明年策劃開設的游戲哲學等,讓立志于學習哲學的學生能以其特有的哲學視角切入生活世界。
除此之外,在學堂班培養計劃的設計中,還特別強化了“哲學+X”的理念,鼓勵學生選修跨學科課程,尤其是非人文學科,力求打破學科壁壘,使學生獲得更廣闊的知識視野,理解哲學在多領域中的應用和融合。
與哲學重新對話
在績效主義盛行的今天,人們總在問,哲學還能帶給我們什么?夏瑩告訴我們,哲學帶來的是一種清醒的痛苦,這種痛苦源于對問題本質的深入理解。當人們越深入地理解某些問題,越會意識到改變它的艱難和自身的局限,甚至產生無力感。正因為如此,哲學常常讓人走得緩慢而謹慎,在這個過程中,人們不得不面臨痛苦,卻又無法輕易逃避。
因為不管如何痛苦,哲學都是人類的精神家園。只要人們的存在中兼具思想與肉體,這種對哲學的需求便不會消失。也許不是所有瞬間,但人的一生中總有一瞬間與哲學有關,或遲或早。畢竟哲學為世人提供了一種不可替代的思想歸宿,是我們理解自己與世界的根基。
黃昏已至,貓頭鷹再次起飛。但夏瑩沒有回到壁爐前沉思,而是選擇打開劇場的燈。
“我學哲學不是要匍匐在哲學門下遵從它所有的東西,這固然是一種方式,但慢慢跟隨它走過來,我希望有一天能和它站著平等對話。我們不可能固守傳統,要一直創新,要走向未來,這樣才會有希望。”
蘇格拉底的吊籃終會降落地平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