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原標題:從中專生到北大博士,副教授的他逆襲半生,卻倒在52歲:雙非高校教師承受了太多 2025年3月11日,洛陽師范學院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陳巍的生命定
原標題:從中專生到北大博士,副教授的他逆襲半生,卻倒在52歲:雙非高校教師承受了太多……
2025年3月11日,洛陽師范學院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陳巍的生命定格在52歲。
一場跨越30年的逆襲:中專防疫員、北大博士、日本學專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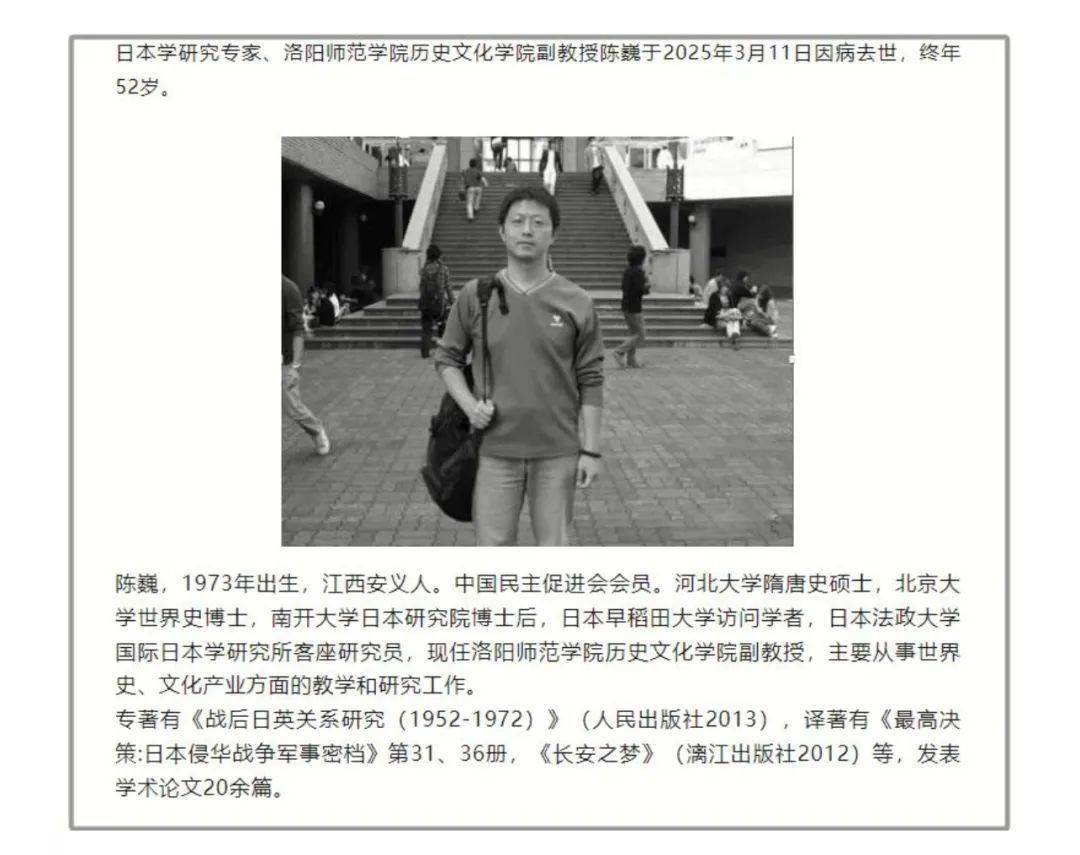
據悉,陳巍是日本學研究專家,多次赴日本學習。
他的故事始于江西小城的中專生,終于象牙塔里的學者——這中間,是一場關于“不甘平庸”的史詩級逆襲。
1995年,中專畢業的陳巍被分配到防疫站工作。 1995年中專畢業,是什么概念呢?92年考上中專相當于現在考上中等211到中等985的水平(要看中專學校和專業),97年以前,那時候中專畢業可以直接分配到煙草局干部待遇,給編制等豐厚待遇。可見,在那個年代,中專畢業已經是優秀人才。
然而,日復一日的機械生活讓他焦慮:“難道我的人生一眼就能望到頭?” 他拿起計算機考研書籍,卻鎩羽而歸。
命運的轉折點出現在他轉向歷史學:2003年考入河北大學隋唐史碩士,后以北大世界史博士、南開大學博士后的身份,成為日本學研究專家,并赴早稻田大學深耕學術。
學生評價他:“幽默博學,心如赤子”,但鮮有人知,為了博士論文,他曾自費2萬元在日本掃描史料膠卷,通宵達旦整理檔案。
從防疫員到北大博士,他用了15年;從博士到病逝,他只有15年。
學術“狂人”的遺產:20篇論文、百萬字譯著,與未完成的日英關系研究
陳巍的學術生涯短暫卻璀璨。他留下專著《戰后日英關系研究》、譯著《日本侵華戰爭軍事密檔》,以及20余篇CSSCI論文,篇篇指向冷門領域——戰后日英外交、唐朝與日本關系、新加坡對日索賠。 從2011年開始到2023年,陳老師一共在期刊上發表論文16篇,其中C刊正刊一篇,C擴和C集期刊約有三四篇,其他基本上都是專業性還不錯的普刊。而且 從2014年以后,陳老師所刊發的論文,就基本上沒有所謂的核心期刊了。
他的研究有多“硬核”? 為了考證日英復交細節,他翻遍日本外務省檔案;為了還原唐朝與契丹的交往, 他幾乎“住”在圖書館。
同事感慨:“他總說‘歷史是活的’,卻把自己熬成了史料。” 然而,這樣一位學者,生前生活簡樸。家中擺設簡陋,手術后的慰問金5000元成了他最大的支持。
學術的光環下,是清貧與孤獨。
“非升即走”背后:高校教師的生死時速
陳巍的離去,撕開了高校“青椒”(青年教師)的生存真相。
盡管他避開了“非升即走”的考核(洛陽師范學院未實行該制度),但高壓仍是常態: 教學、科研、論文、項目“四座大山”,讓許多教師喘不過氣。
有高校教師自嘲 :“我們不是在寫論文,就是在找數據,連生病都是奢侈。”
數據刺痛人心:2025年僅前3個月,就有52歲的陳巍、41歲的南師大副教授宋文文等多位中青年學者病逝。一位匿名高校教師留言:“評職稱就像跑馬拉松,但裁判在你耳邊喊——跑不過,就出局。”
陳巍的故事,是逆襲的贊歌,也是制度的警鐘。當學術理想撞上生存壓力,高校教師的“生死疲勞”誰來買單?
膠質瘤奪命的365天:最后一堂課,他還在講臺上
陳巍的病因是膠質瘤——一種兇險的腦癌。
學生回憶,2023年10月他最后一次上課時,已面色浮腫,聲音沙啞,卻堅持講完《日本近代外交史》。 病床上的學者,仍在掙扎: 術后他接受慰問時,桌上還擺著未完成的書稿;去世前一個月,他給學生的郵件里寫道: “若時間夠,我還想整理早稻田的檔案……”
這不是孤例。南京師范大學80后副教授宋文文,同樣因過度勞累患重病離世,年僅41歲。
寫給大家:學術圈不需要“殉道者”,我們需要活著的光
陳巍用半生逆襲證明:知識能改寫命運。
但他的早逝也提醒:健康才是最后的底線。
沒有販賣焦慮的意思,初衷只是希望敬愛的高校教師們,請記住—— 定期體檢。就像膠質瘤早期癥狀易被忽視,頭痛、視力模糊需警惕。
想對大家說,拒絕“自我剝削”:深夜的臺燈很美,但凌晨的月亮不該成為標配;
學會“不完美”:一篇論文可以晚交,但生命不能重來。
陳巍的電腦里,還留著未發送的課件。
最后一頁,他寫道:“歷史教會我們反思,但愿我們不止于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