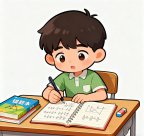摘要: 原標題:人在外企,一代人有一代人要下的崗 以前,我們總以為穩定是外企文化最重要的一部分。 直到經歷了裁員,才明白外企那所謂的穩定,都是虛幻
原標題:人在外企,一代人有一代人要下的崗
以前,我們總以為“穩定”是外企文化最重要的一部分。
直到經歷了裁員,才明白外企那所謂的穩定,都是虛幻的,有也只不過是階段性的穩定而已。
回頭看外企在中國的30年,在不同的時間里,熙熙攘攘的人們走進了外企那華麗的門廳,同樣也有很多人絡繹不絕地離開了這里。
其實并沒有所謂永遠的穩定,即便當年號稱永遠不倒的國企,也在外企進入的那個90年代,沒能逃掉慘烈的大下崗,而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如今外企人的“下崗”也如波浪般一浪接著一浪。
最終我們或許都得明白:打工人,一代有一代要下的崗,外企也不除外。
在下崗這件事前,資歷,能力,努力或許都不是最主要的因素,是時代、戰略和業務表現的綜合結果。
01 90年代末,第一代外企下崗人
90年代是外企進入中國的最早期,業務高歌猛進,福利優渥,有很多人想都想不到的辦公環境,堪稱當時打工天花板。
但是幾年后,有部分公司發現市場并沒有預期得那么理想,市場需求放量來的有些慢,全球總部開始了收縮業務。
公司里有位老同事Jack,分享過他所經歷的那個年代的故事:他說他當年算是公司第一批員工,業務初期,親歷了公司從幾個人到幾百人的快速擴張。
彼時,他以為自己一定能在這里干到退休,畢竟那會連美國總部的市場VP都曾給他頒發過大獎,記得他的名字。
可在2000年左右的一個下午,他收到了外企生涯里第一份裁員協議,上面寫著醒目的“業務調整”幾個大字,不過通篇沒有質疑他的績效,只提到:“總部決定撤掉亞太的某條產品線”。
離開那天,Jack在空曠的辦公室里,把當年公司發的獎杯全部塞進紙箱帶回了家,他覺得那是他人生不多的高光時刻。
雖然下了崗,但外企自此成了他的職業信仰,從此非外企不進。
02 2008年,第二代外企下崗人
第二次大規模外企裁員潮,出現在2008年前后。這次裁員,問題來自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作為布局全球市場的外企,受到的沖擊最大,而當總部的日子不好過時,各個BU的開源節流是必然的,其中降本最直接的方法,裁員常常是那個最優先選擇。
HR在會議室進行一對一的談話,桌上是厚厚的解除協議和冰冷的簽字筆,HR皺著眉頭簽下的最終名單里,不一定都是業績最差的人,也有許多“年度最佳員工”。
很多人終于明白:本以為手握巨大市場的BU,充其量也只不過是全球布局中的一個節點,當總部決定調整布局時,并不會因為你有過多大的榮譽,背多少的房貸,要面對什么樣的生活危機,就網開一面。
從那刻起,外企人心中的外企開始變得有一點冰冷了。
03 2015年起,第三代外企下崗人
進入2015年之后,外企的下崗變得頻繁,一個個部門、一個個職能在悄悄消失。
但這次的原因非常簡單,因為總部發現,如果把同類業務交給本土團隊,將獲得更激進的目標、更便宜的成本,也更容易抓住本土市場。
總部最后的決定是:與其繼續投入高成本外籍管理和架構,倒不如用直接啟用本地化架構+外包來完成工作。
市場部同事Sara就曾給我分享她之前公司的故事:她曾是前司的“明星員工”,作為市場部設計高級經理,帶的團隊雖不是很大,但卻精英云集,薪酬不低。
隨著中國區業務競爭越來越激烈,市場部承受的壓力越來越大,最終公司做了一個讓所有人都意外的決定:把設計業務整體外包給了一家本土公司。
雖然最后的結局是大家都拿著豐厚的補償離開,但當時的她仍感慨萬千:“看著那些外包公司的人走進辦公室,坐在原來團隊們的工位上,那一刻,她好像看見了十年前的自己 ……只是現在的她,成了被外人取代的人。”
04 一代人的下崗,是一代人的上崗
戲劇的是,每一波被裁的“老一代”,都曾在當年看著前輩離開,心里想的是:“我還年輕,前方有無限機會和可能”; 殊不知若干年后,坐在那把椅子上的人,卻是自己。
外企早已沒有了絕對的穩定,也做不了永久的飯票,它的魅力只在于:你處在它的周期里時,將獲到成倍的成長、收入和視野,殘酷的是,當周期結束時,就得好好考慮如何下車的問題。
面對這條“必經之路”,我們能做些什么:
保持持續學習和跨界的能力:職位會消失,但個人的能力卻可以延續到新的行業和崗位。
不要只做一個專家:想辦法把自己的專業知識,外化為行業的通用技能。
關注趨勢而非頭銜:頭銜往往不可持續,只有市場的趨勢,才決定了下一份工作在哪里。
做好財務規劃:多準備一些GAP期緩沖金,給自己從容尋找下一步的時間和安全防護。
在外企,這是周期,也是不得不面對的現實。
一代人有一代人要進的場,一代人有一代人要下的崗。
只是可以輕松一點,別把離開看作失敗,這或許只是你和外企不得不錯過的一段旅程。
正如一位前同事在離開外企時說的話 :
“作為打工人,能在這個國際舞臺經歷幾年,就覺得很值得,即便這一段旅程暫時謝幕,但收獲了滿滿的底氣與信心,每代人都有自己要面對的時代,
但下了外企的崗,我們照樣可以江湖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