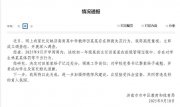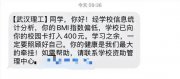摘要: 原標題:退休12年后,一位高中老師在抖音講語文課 人家說七八十歲是人的智力高峰,我還沒老呢。一位73歲的退休教師說。2024年秋天,他開始通過短視頻
原標題:退休12年后,一位高中老師在抖音講語文課
“人家說七八十歲是人的智力高峰,我還沒老呢。”一位73歲的退休教師說。2024年秋天,他開始通過短視頻平臺分享高中語文知識。一年后,一群年輕人在娛樂化信息汪洋中注意到了這位“老年闖入者”。新奇、調侃之后,一場跨越時代鴻溝的相互理解與對話,出現了。
語文老師的感覺
打開抖音,一位老教師在上語文課。

他神情嚴肅,語速平緩,語調沒有明顯起伏。除了開頭的一句“大家好”,近10分鐘的視頻里,找不到一句與教學內容無關的閑話。嚴格意義上來說,“大家好”也算不上閑言贅語——這是傳統(tǒng)課堂禮儀的一部分。
舉手投足間,他身上的老派作風盡顯。反光的眼鏡時不時滑落到鼻梁中段,兩句話的間隔,諸如“啊”“這個”的口頭禪頻繁冒出來。他沒有剪掉任何停頓和磕絆。
在最初錄制的視頻里,一塊小白板或者黑板總是擺放在他身后,上面用黑色馬克筆或者粉筆手寫著板書。古樸的個人特色也體現在他的著裝上——他總是穿著襯衣搭配一件舊西裝外套。“老師真的很認真對待錄視頻課這件事,還穿了西裝。”有心網友意會了這個細節(jié)里的誠懇與敬畏心。
這個叫作“高中語文王老師”的賬號主頁顯示著他的年齡——73歲。他曾是哈爾濱一所中學的語文老師。去年10月,在退休的第12年,他開始在抖音講語文課。
如今,試水視頻博主一年了,鏡頭里的他明顯松弛下來。白板和黑板漸漸出現得少了,他也不再以一種線下講課時的板正站姿出現在視頻里。西裝換成了毛衣,而后是一件鼓鼓囊囊的棉襖——那是冬天了。
他開始像網上任意一個游刃有余的自媒體博主一樣,隨意地將鏡頭對準自己的臉,或者電腦屏幕,隨時隨地進行內容生產。
一些細節(jié)又凸顯著他與這個光怪陸離的平臺之間的格格不入:沒有美顏濾鏡的修飾,沒有喧鬧BGM的氛圍烘托,只是一位毫不掩飾歲月痕跡的老教師,在不疾不徐地講解著高中語文知識,之乎者也,實詞虛詞,娓娓道來。
如果不是一條發(fā)布于今年8月份的講課視頻突然獲得了超千萬的流量,很多早已遠離應試教育的成年網友或許不會注意到他。
“怎樣寫好議論文”,視頻畫面上方標注著醒目的紅色標題。這條時長為6分46秒的視頻,因流量效應,引來大量“非目標用戶”圍觀。彈幕和評論區(qū)里充斥著年輕網友的熱烈反饋。
“講得真好”,“謝謝老師”,一些認真的學生熱情有禮。
“老師這么大年紀出來做抖音,是缺錢了嗎?有困難跟大家說,大家一起幫忙。”有熱心的網友關心他的生活處境。
“困了”,“應該打上助眠標簽”,“廢話,還用你說”,這些不友好的聲音是另一種。隨手打出的輕率與無禮,和年輕人以調侃、抽象、幽默之名習以為常的互聯網表達習慣,混雜在一起,在嚴肅認真的知識類分享視頻下,成了一種冒犯。
很快有網友意識到了這一點。一種討伐冒犯者的聲潮漸起。
“老師,大家說聽困了,只是說老師很有語文老師的味道,很正,有種國泰民安的感覺。大家是開玩笑的,老師不要傷心。”有網友在評論區(qū)解釋。
海量評論,他大多數沒能回應。但這條善意解釋他回復了。
“原來如此,謝謝你,本來想刪帖的!”原來,那些攻擊老師是能看見的。確認了這一點后,更多的安慰和支持評論涌了進來。
玩抖音
那是8月的一天,王老師發(fā)現自己那幾天的粉絲量增長很快,每天增量四五千,眼看就要突破10萬。玩抖音不到一年,他陸陸續(xù)續(xù)發(fā)著視頻,還試過3場直播,但賬號始終冷清,關注人數從十多個漲到兩千多個再也不動。6月高考結束后,“粉絲還掉點”。
他猜想,這突如其來的熱度或許和自己前段時間空閑增多,更新頻率上升有關。對年過七旬的老人來說,很多事情,要弄明白總需要花更久一點的時間。率先出現在腦子里的是一些更質樸的想法。“‘火’起來之后我就有信心了,還接著整我那一套吧。”
直到收到采訪邀約,他才得知自己的視頻在其他社交平臺引發(fā)了熱議。他馬上追問:我怎么能從其他平臺看到對我的討論呢?
對于互聯網世界里的新事物和新現象,他保持著一種難能可貴的好奇心。
一年前,他發(fā)現抖音上有很多老師在講課,語文,數學,英語,各種學科都有人講,聽的人也多。“這是挺好的方法啊,那上面受眾廣啊,你在那講課,很多人都能聽著啊。”他想。
他也注意到,講課者大多是年輕人,歲數大的是少數,而且,“所謂歲數大,也都比我年輕”。這不是問題,他決定試試。一念之間,一次新的探索之旅就這樣開始了。
一個麥克,一部手機,就是全部的拍攝設備。至于生產的內容,他沒有做特別周密的長期規(guī)劃,從高中語文知識中挑幾個考生最關注的難點來講,總沒有錯。于是第一節(jié)課,主題是文言文的被動句。
分享的干貨都是畢生積累,但對待視頻拍攝,他依然奉上了最高禮儀。小黑板和白板都是專門買的,最初的襯衣和西裝也是特意換上的,為了上鏡時“像那么回事兒”。他花了一些時間琢磨創(chuàng)意構想,將腳本寫下來,這才開始錄制。
說是會拍視頻,但他也只是會“一拍到底”,用他自己的話說,是“最簡單、最笨的辦法”。先錄一遍,自己看一遍,發(fā)現哪里有磕絆,講錯了,或者有其他任何瑕疵,這條就“廢了重拍”。一遍一遍,直至自己滿意。他還沒有學會如何剪輯視頻。
有學生提醒他,可以加上字幕。他去網上搜索教程,“費很大勁啊,最后整明白了”。他學會了用剪映加字幕。于是又將從前發(fā)布的點擊量低地沒有字幕的視頻隱藏起來,加了字幕重新發(fā)。“重新發(fā)點擊就挺多,很多人都看。”關于視頻創(chuàng)作心得,他又總結出了一條。
如此一來,說是用最簡單的方法做視頻,實際花費時間也不少。他習慣夜晚錄課,晚上9點多開始工作,到視頻最終發(fā)布成功,就已經過了夜里11點。
這一年來,他一點點摸索著,改進著,也慢慢悟出了一套屬于自己的自媒體運營經驗:衣服可以穿得隨便一點,黑板白板都不是必需的,攝像頭也不必非要對著自己的臉,講稿直接顯示出來,這樣,學生就都能看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