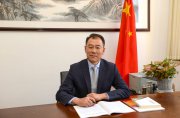摘要: 原標題:中國不只需要985大學 跟訪王樹國的這天,我對一個細節印象深刻:這是南昌的8月,王樹國頂著烈日、風塵仆仆地趕到酒店時已是中午,幾小時后
原標題:中國不只需要“985”大學
跟訪王樹國的這天,我對一個細節印象深刻:這是南昌的8月,王樹國頂著烈日、風塵仆仆地趕到酒店時已是中午,幾小時后,他就要去當地某中學召開座談會。就在午飯的短短間隙,他的大腦沒有片刻休息,一直在憂慮福耀科技大學的未來,他口中反復念叨著:“我們一定不能‘屈服’于傳統的模式,再走回頭路沒有意義。”

王樹國的焦慮基于兩點:一方面,他預判,新技術革命留給我們的窗口期不會太長,到2035年前后,如果人才培養體系還沒有跟上技術迭代的步伐,中國就可能錯過這一輪發展機遇期,因此,對傳統大學的改革不僅勢在必行,而且非常迫切;另一方面,新型研究型大學進行改革,要突破的不僅是傳統的人才培養模式與大學組織制度,還要從根本上打破固有的評價體系,換言之,要改變的是整個高等教育的“游戲規則”。
目前,我國僅有8所新型研究型大學,王樹國很擔心,其他新型大學因為“頂不住”外部壓力而逐漸走回傳統大學的賽道上,而剩下的少數幾所,未來會孤掌難鳴。他的擔心不無道理。迄今,圍繞新型研究型大學的概念、形態、學科框架與體制機制等核心問題,仍有待頂層設計的進一步明確。這意味著,現有的改革仍以自下而上的探索為主。
以選專業為例,幾乎所有新型研究型大學都允許學生在1—2年的通識教育后,不以績點為“門檻”自由選擇專業,但多位負責人對我表達了更理想的改革方案,是參考美國的“完全學分制”:即沒有專業、只有課表,學生完全依據興趣自主選課,可以同時或先后選修多門專業課程,只要修滿對應專業的最低規定學分,即可獲得學位。
這樣的制度保障了學生徹底的自由探索空間,但采取這種做法有兩個重要前提:首先,是彈性學制,在美國,有學生在多次探索、“浪費”一些時間后才發現最喜歡的專業,這可能導致其無法在四年內畢業,但從更長的人生發展軌跡來看,這種“浪費”是成長的必經階段。目前在國內,受宿舍管理、畢業率與升學率指標、社會輿論等多種因素影響,極少有學校愿意真正實行彈性學制。
其次,是學生擁有自主選擇的能力。與美國不同,中國的很多孩子一路從應試教育走來,進入大學之前,幾乎不需要自己做選擇,整個教育環境也沒有提供選擇的機會。因此,多數中國學生不清楚自己真正喜歡什么、擅長什么、能力的邊界在哪兒,進入大學后,面對一張完全由自己來填滿的課表,甚至會表現出迷茫、驚慌。這一階段,大學如果沒有足夠強的介入與管理能力,很容易給學生的發展帶來負面后果。這也凸顯了教育改革的復雜性,改革要環環相扣,大學改革也需要中小學同步進行改革,給學生更多專業和職業規劃上的指導。如果大學與中學的銜接沒做好,僅依靠大學孤立改革,改革越超前,學生需要的過渡期就越長。
新型研究型大學,是一場由老師、學生以及政府共同參與的“教育冒險”。能否走出一條新路,與改革者的決心、毅力和戰略性眼光有關,也與中國高等教育大環境的包容度有關,更與被輿論和就業焦慮裹挾的每個考生及家長有關。
中國未來需要怎樣的新大學?答案或許尚未清晰,但至少我們知道,中國真的不只需要一所新的“985”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