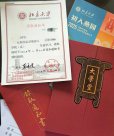摘要: 原標題:教育離職率登頂:你以為的穩定職業,塌房了 6月尾聲,深圳一所中學的臨聘教師蔡蔡被通知:暑假不用來了,合約到期。北京西城,初中語文老
原標題:教育離職率登頂:你以為的穩定職業,塌房了
6月尾聲,深圳一所中學的臨聘教師蔡蔡被通知:“暑假不用來了,合約到期。”北京西城,初中語文老師戴娜在學期最后一天收到了“合同不續簽”的通知。她說,同期入校的老師,已有近一半悄然離開,或被動失業,或主動離職。

另一端,“#老師辭職”沖上熱榜,“#教師抑郁”“#編外清退”輪番刷屏。評論區不再是調侃,而是密密麻麻的“我也是”。一個職業的集體告白,被夏天的熱浪推上顯影層。
很少有人意識到,講臺上下的裂痕,早已顯露在數據中。2025年6月,《薪智教育行業白皮書》公布:2024年,教育行業平均離職率為20.8%,超過零售(19.4%)、房地產(18.7%)、互聯網(18.4%),位居所有行業之首。
過去六年,教育行業連續躋身全行業離職率TOP5,自2020年后,再次登頂。這幾乎成為一種常態。而離職,往往只是故事的開頭。
曾被視為“最穩定”的職業,為什么開始頻繁流動?一個行業的高離職率,背后究竟在松動什么?
當越來越多教師悄然離開講臺,我們是否忽略了某種更深層的變動?
離開的,都是誰?
北京西城區的初中教師戴娜,是以“編外合同”的身份入職的。研究生畢業那年,她滿懷期待地進入一所重點中學,做過班主任、帶過兩屆中考。但今年暑假前夕,她收到通知:“合同到期,不再續簽。”
“編制在崗不在身。你只是學校的臨時變量。”她苦笑著說。教學任務不輕,責任不少,唯一缺席的,是職業的確定性。
在教師圈,這被稱作“期末前的哀悼”,講完最后一節課,就默默清空抽屜。
類似的“清退通知”正悄然蔓延:
“我在重慶沙坪壩,中學非編老師,已經被裁了。”
“石家莊開始批量清退勞務派遣老師,保定還會遠嗎?”
“永州,代課一學期,數學兼道法和體育,接到通知下學期不用來了。”
“西安的第三方派遣教師,開始簽署‘自愿離職協議’,爭取考編上岸前別輪到自己。”
如果說,編外制度是一次“安靜的抽身”,那么教培行業的離職,更像一場倉促的撤退。
“十年教培,大廠五年,創業五年。真扛不動了。”
“五人小班,底薪3000,課時費總共1200,扣完社保剩3800。”
“被當服務員對待,家長投訴,老板扣錢,沒尊嚴。”
“年后新崗干兩個月被裁,斷斷續續做招生顧問,正準備辭職。”
這不是個體的不適應,而是系統更新時對邊緣崗位的集體性清算。2024年,教育行業平均離職率達20.8%,高于全行業平均(16.8%)近4個百分點,躍居各行業之首。細分來看,民辦教育(21.1%)和職業教育(21.4%)是將總體數據推高的關鍵板塊。
這組數據的底層,是2572家民辦學校、2139家職業教育機構、5953家非學科培訓企業作為樣本,它們大多不具備“穩定”的能力,也不承諾勞動合同的長久性。
這些“失約”的背后,是具體而密集的日常在默然解構。
蔡蔡在深圳一所知名中學任教,每天帶三個班,負責社團、家訪與晚輔。放假前,她收到短信通知:“合約到期,暑假不用來了。”她明白,這不過是勞務派遣制度的慣常處理,既無補償,也不解釋。
另一頭,戴娜穿越整座城市通勤,在地鐵上批改最后一疊作業。她說:“不是失望,而是當初信得太滿。”如今,她在準備別的系統考試,“不是因為理想,而是害怕再被清退。”她頓了頓,“你以為你在做教育,后來才明白,你只是這個系統里一個隨時可以移除的人。”
他們不是“躺平者”。相反,很多離開者正是最早也最深地投身教育的那群人。他們寫過教案、扛過心理危機,也陪學生走過青春低谷。但最終,在合同、考核與邊界之間,他們耗盡了繼續留下的可能。
他們的離開沒有聲響,只是一條持續上升的數據曲線,悄悄劃過盛夏的尾聲。
暑假鈴聲響起,離職序幕拉開
七月初,韓一鳴遞交了辭職申請,內容只有兩句話:“本學期教學任務已完成,請盡快辦理離職。”
打印、簽字、蓋章,流程順滑得像刪除一段冗余代碼。他發現,自己這個“非全日制教培講師”的存在,在公司系統里不過十幾個字節。沒有評估、沒有告別,沒有留下任何痕跡。像從未被真正需要過。
他畢業于西部某師范大學中文系,2021年入職一家民辦教培機構,主講中學語文。“雙減”后,公司將應試課改名為“大語文表達力”“古典詩詞賞析”“戲劇化閱讀”,試圖靠包裝留住市場。但學生銳減、班次縮水、課時浮動成了常態。他最初的“以教學為本”很快被瑣碎擊穿:加班、招生、家長答疑、后勤支援,一個不落。
“我們組八個人,三年走了五個。”韓一鳴說,“留下的三個,一邊帶班,一邊天天八點半開會。早上帶讀,中午講座,晚上報課會。有時候,一天要打五十個家長回訪電話,不打完不準走。”
最初,韓一鳴常在深夜批改作業、備新課,寫下幾百字的教學反思發到組群。后來,他只發幾個表情包敷衍。同事以為他“看開了”,他卻明白,那不是釋然,是熄火。
臨走前的幾個月,他感到一種情緒的鈍化。學生表現不佳,他不再焦慮;家長語氣尖銳,他懶得解釋;臨時被調課,他連拒絕的語氣都省了。“像一口沒蓋緊的熱水壺,”他說,“熱氣全跑光了。”
真正讓他決定離開的,是某天深夜的一次自問,他已經半年沒讀完一本書,也很久沒有寫下一段屬于自己的文字。“我教學生如何表達自己,”他說,“可我自己,已經不表達了。”
趙昕昕落選了期末評優。她并不意外。在那所市屬小學,她是唯一的編外語文老師。指標有限,優先照顧體制內,幾乎成了慣例。
但她仍感到些許羞恥,不是因為落選,而是因為落選已被視為理所當然。
她33歲,碩士畢業,2018年通過人才引進入職深圳。六年來,年年承諾“轉編有望”,年年無果。
2024年下半年,區教育局發布通知:三年內壓縮臨聘比例,推行“崗位聘任制”。學校據此組織編外教師能力測評。她參加了,成績不差,仍被列入落聘待定。
她問校長是否明年不能續約了。校長沒有正面回答,只說:“可以考慮轉到協作單位,比如社區托管中心,或者校外素養基地。”聽上去好聽,實則“編外再編外”。
她在朋友圈寫下這句話:“對很多編外老師來說,期末鐘聲不是休息的開始,而是失業的倒計時。”她形容自己像一只未封口的行李箱,哪天箱子倒了,“成績”“陪伴”“成長”都會掉出來,散落一地。
韓一鳴流向市場,趙昕昕困于體制邊緣。他們的共同處境是:教育系統不再具有承接力。
梳理三十余份縣域教師招聘公告,超過六成明確標注:“臨聘不得轉正”“合同一年一簽”。有縣區要求教師自繳學校應承擔的社保費,有地區將教師“派遣化”,人在講臺,勞動關系卻掛在校外公司。
這不是一場個體的情緒危機,而是一種結構性的沉降。穩定崗位越來越少,短期合同、高替代性、有限保障、流程壓強逐步取代了托舉與培養。失穩的不只是職業,還有情緒、信任,以及那種被延遲表述的心理塌方。
浪潮中的職業遷徙
2015年4月,好未來在北京推出“1元一科”的新初一暑期班。此前,新東方優能早一步將數學走讀課降至50元。高思教育則干脆將數學、語文、英語統統作價1元。
家教O2O在這一年達到鼎盛,品牌數量峰值超過100家,現金補貼戰迅速蔓延。上半年,輕輕家教發布獎勵機制:推薦一位新學生下單,獎100元;推薦一位新老師搶單成功,獎30元,多推多獎。一張“教師收入排行榜”在圈內瘋傳:前二十名教師的月收入在三萬至七萬之間,最高扶持金額超過萬元。到了9月,輕輕家教宣布停止對老師的補貼。
從出生起即“人人喊打”的教育O2O,在一場虛火中迅速燃盡。六年后,輕輕教育被曝疑似“跑路”,老師們一夜間被清理出微信群,仿佛從未存在。
時代的大幕,已經拉開。
2019年,一度被人們稱為教培行業過去十年里最差的一年。超過1.2萬家教育公司關停,成教和早教成了跑路的重災區。年初,俞敏洪親點孫東旭擔任新東方在線聯席CEO,四年后,“孫美麗”在直播間開會摔手機,觸發了東方甄選小作文事件的連鎖反應。與此同時,好未來市值增長81%,逼近2000億。
猿輔導、作業幫、跟誰學等推出暑期低價課,喊出“數十億廣告投放,1000萬人次參培”的豪言,僅學而思網校一家投放就超過了10億元,張邦鑫親自買猿輔導的暑期體驗課,將輔導老師服務流程截圖給團隊,研究猿輔導在抖音的投產比。
這場大戰使流量進一步枯竭,獲客成本飆升,行業內的馬太效應愈發明顯:中公教育借殼上市,成為A股第一職業教育股;斑馬英語被爆單月營收破億;屹立市場20年的韋博英語轟然倒地;龍文教育對賭失敗被起訴。
8月,一封題為“VIPKID數據造假”的郵件發到了幾位潛在投資者的郵箱,發件人是VIPKID原法務、財務和戰略組成的三人小組。該說法遭VIPKID否認。2019年,VIPKID的獲客成本幾乎翻倍。盡管10月完成了一筆重要融資,但11月傳出裁員15%-20%的消息。人們開始擔憂:如果VIPKID撐不住,整個行業都會崩掉。
裁員潮從年初就開始了。3月,滬江網校因對賭失敗裁員50%;4月,頭條系的Gogokid裁員70%-80%;11月,西瓜創客裁員60%;12月,作業盒子裁員40%以上。
同年9月,一位署名為“有良心的韋博英語員工”的帖子迅速在網上傳播,揭開了韋博英語多地校區拖欠員工工資并停止運營的驚雷。創始人高衛宇隨即清空社交賬號。10月12日,高衛宇發內部信稱,因業績惡化、資金鏈斷裂,公司已無法履約,旗下開心豆英語已由新投資人接盤。他表示,若日后有能力,將為員工補發欠薪。
這封信引發了巨大的爭議。當高衛宇再次出現在公眾視野,是在銀行轉賬被認出,隨即被一群維權學員團團圍住。
韋博只是這場危機中的一個典型。同時倒下的,還有成立18年的太傻留學、兩年內完成四輪融資4億元的成長保、曾風光一時的O2O平臺瘋狂老師,以及新東方名師創立、好未來投資的朗播網。
2021年春晚,猿輔導向觀眾發放了1000萬份“知識福袋”。小品《陽臺》里,佟大為和王麗坤飾演的教師夫妻家中,陽臺上掛著字母表,下方赫然是偌大的猿輔導logo。春晚主持人在節目間歇鼓勵觀眾去抖音領取燈籠紅包,燈籠點亮時,高途課堂的名字赫然在列。大年三十,瓜瓜龍宣布章子怡成為代言人;大年初一,51Talk與王俊凱的雙語祝福占據微博熱搜第三位。
儼然一副紙醉金迷的黃金時代。
6月,局勢發生了變化。教培圈傳來一則消息,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稱,“相關部門將出臺前所未有的規范文件,整頓民間教育培訓行業,限制廣告,并試行假期期間禁止補習。”這條消息未引起太多關注,人們將其視作“路邊社”傳聞。
一個月后,2021年7月21日,一則被稱為“40號文件”的文件在很多教培群里瘋傳,一場暴風雨即將來臨。
7月22日至23日,美國上市的中概教育股集體暴跌:高途跌59%,新東方跌58%,好未來跌57%,有道跌36%,洪恩教育跌21%。許多公司市值腰斬。7月24日晚上7點,《關于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正式發布。
新東方和好未來相繼宣布停止義務教育階段學科類校外培訓服務。俞敏洪把桌椅板凳都捐了。千億市場驟然消失,數以萬計的員工被裁撤。這是一場職業遷徙的迫降。從K12科目到非學科素質類,教培人員宛如一群系統之外的人,集體被歸類進另謀出路。不少人轉去直播帶貨、保險、家政服務,還有人轉型做編程課推廣員。
當新一輪的教育變革浪潮襲來時,那些離開和正準備離開的人,依然在這片時代的浪潮中浮沉。教育,它仍然在那里,但已不復往日的模樣。它的未來,或迷失在無盡的風浪之中。
流動的鏡像:當教育變得像零售
學期中后段,一家民辦高中發布教師招聘啟事:“月薪7000,三年合同,每年續簽一次。”評論區里,有人問:“年終獎、績效怎么算?”招聘方回復:“暫未設立。”再往下翻,有評論說:“不如去瑞幸。”這不是一句玩笑。
2023年,某咖啡品牌在高校附近招募“大學生儲備店長”,底薪7000元,月休八天,三個月轉正,一年后可帶團隊。教師求職和咖啡面試,出現在同一個朋友圈。
自前文提到的那組20.8%數據再向下細看,會發現教育的流動曲線不僅高位,而且與餐飲、零售、互聯網交替霸榜。過去五年,這五個行業的排名在“離職率TOP5”榜單中反復交替,幾乎成為中國勞動力流動性的主力板塊。
離職率從不是孤立的數據,它是結構變化的體征。行業流動性上升,通常意味著供需錯位或職業價值感的滑坡,尤其是對教育這樣的公共職業。
零售批發行業的高流動性,一般與流水線勞動、低附加值、年輕勞動力替代性強等因素相關。嚴格的時間打卡、流程指標、標準化話術,構成了一種工業式勞動邏輯。這個問題正越來越多地指向講臺。
在體制內,編外教師、臨聘教師,尤其是基層的“代課”教師,也在面臨著類似的命運。
湖北鄂州市為應對生源減少和教師過剩,實行“進一退一”,2023年起大幅減少編內教師的招聘。
2025年3月,江西省萬年縣暫停招聘英語教師。南昌進賢縣在上一年已經因為 “編制限制” 全面停招。多地啟動教師分流、退出機制:湖南湘潭縣清退500名編外教師,衡陽選調100名教師至其他事業單位;
黑龍江鶴崗則分流206名教職工至研培機構和社區教育中心。貴陽推出“末位淘汰”制度,三次考核不達標的教師將被解聘或調崗。
據不完全統計,全國已有超10個省市啟動“教師退出機制”,轉崗、待崗、解聘不再停留在紙面。
教育管理體系開始與零售、餐飲行業趨同,通過考核、績效數據和定期人員流動,教師的角色從知識傳遞者轉變為流程中的一環。
一個教師說:“我不是因為累才想走,是因為不知道自己為什么要留下。”她曾相信教育是一項意義驅動型職業,承載著連接、改變、陪伴。但如今,她被量化為績效數據的一組小數點,被課堂評分的KPI左右情緒。她說:“我講一堂課,像是在完成一張數據報表。”
在越來越多學校中,“人”的管理正被平臺化系統替代。每一項任務都可視、可量、可控,卻難以觸及“為什么而教”的問題。教師的工作形態,從“專業性勞動”向“流程性勞動”退化。
一位資深教師說:“以前靠教學贏尊重,現在是看誰上傳材料快、發通知全、家長群不出事。”她帶的是畢業年級班,壓力極大,卻仍要每周應付行政任務。她說:“像不像店長?”是的,像極了。一個教育系統的責任人,變成了流程管理員。
教育這一傳統上承載精神性與公共使命的領域,正被工廠邏輯滲透,它所承載的象征資本在流失,被置于一種新的評價秩序下:產出多少、留痕是否、指標是否合格。在“教學管理平臺化”“考核量化”“學情數據可視化”等趨勢之下,教師的工作形態正被“工業性指標”定義,也就不再享有超越性的信任與尊嚴。
這就是為何,當教育行業的離職率逼近甚至反超零售、餐飲、制造業時,它所昭示的,不只是一個職業群體的疲態,而是更深的社會裂隙。
我們正在經歷的是一個意義坍縮的年代。看似有意義的崗位,無法提供情感回報;看似無意義的崗位,在榨干體力和心理空間。原本位于價值光譜兩端的行業,正朝著相同的勞動意義和管理邏輯靠攏,成為同一硬幣的兩面。
當教育和零售的離職率交匯在同一張榜單上,人們真正焦慮的,是這個時代還能給“有意義的勞動”多少時間。
教育離職率,是一個時代的鏡面
韓一鳴最終沒有回到講臺。他轉行去了一個社區文化服務中心,寫活動策劃、編排節目、組織志愿講座。他說:“還是跟教育差不多的事情,但沒有人再盯著我上了幾節課,錄了幾條數據,有沒有被投訴。”他說這話的時候,眼神松弛,像一個剛剛逃離訓練營的人。
然而,逃離從來不是終點。
在體制編制有限、教培大退潮、民辦合同短期化、績效量化考核的多重擠壓下,教師職業在入職門檻高與穩定性低之間拉開了極大的張力。
很多離開的教師,并非因為“不想教書”,而是因為“教不下去”。他們面臨一年一簽的合同,動輒雙倍績效考核與家長滿意度評分,教學之外的大量無償任務,以及動不動就“優化”或“輪崗”的調整。他們并沒有選項,只有退出。
韓一鳴的離開不是職業轉換,而是“在不能再做教師之后,找到了一個還過得去的地方”。而正是在這種結構性失配的持續累積下,教師職業的另一種意義也悄然瓦解。
長期以來,教育行業靠“社會尊敬感”維系其象征資本。即便工資不高,任務繁重,人們依然認為這是一份值得的職業,因為它承載著傳承、信任與未來。
但今天,越來越多的教育者被視作服務者,而非育人者;被要求提供結果,而不是過程;被量化、考核、替代,而不再被信任、支持、尊重。很多教師說:“現在的家長是客戶,而我們是被投訴就扣績效的前臺。”
當一個職業的象征資本被消解,其意義也不再屬于職業者自己,而是被績效表格、家長評分、管理平臺所定義。
2019年起,伴隨房地產收縮、互聯網退潮、青年就業收緊,教育培訓一度成為高學歷者的避風港。無論是碩博士進民辦,還是985畢業生考編制,人們曾以為講臺是一個可以停靠的地方。現實很快顯露殘酷:崗位高度集中、編制大幅收緊、編外短聘泛濫,再加上“雙減”后教培收縮、民辦規模壓縮,教育的吸納能力迅速失衡。
教育行業進入“高進、高耗、高退”節奏,教師不再是穩定的代名詞,而是“不確定人生狀態”的典型。
如果一些教師的離開是個體命運的悲傷片段,那么當超過20%的從業者集體轉身,就已不是職業問題,而是社會的結構病灶。無論數據是否精確,它所映照的現實依然成立:越來越多教師在離開,而我們正在失去理解他們為何離開的能力。
回看過去十年,中國社會經歷了多次重大結構調整:教培行業急剎車,非公教育生態改變,地產去杠桿帶動教育投入波動,技術將教學算法化,公共危機動搖社會信任。這些因素疊加在一個曾經承載最大公共情感寄托的行業上,教育系統的裂痕,不只是教育系統本身的事情,而是這個社會如何對待“育人”這件事的態度轉變。
一旦人們不再相信教育,教育還如何育人?正如哈貝馬斯所說:“當系統邏輯侵蝕生活世界,當工具理性壓倒溝通理性,社會便會失去對人的基本理解。”教育不僅僅是產業,更不是指標,而是社會如何想象自己未來的一種方式。
今天,在風中搖晃的不是一群教育從業者,而是社會對于人的承接力。如果教育一旦無法承接人的成長、信念與歸屬,那么我們終將喪失對人本身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