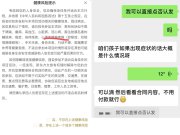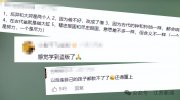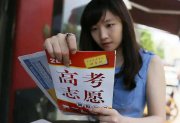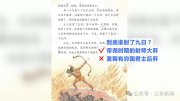摘要: 原標題:大學反內卷,北大先動手了? 作為教育改革的先鋒,北京大學走在了國內大學的前列。而對于其他高校而言,績點可能更是一個既讓他們感到焦慮
原標題:大學反內卷,北大先動手了?
作為教育改革的先鋒,北京大學走在了國內大學的前列。而對于其他高校而言,績點可能更是一個既讓他們感到焦慮,又無法徹底割舍的存在。
北京大學的一紙公告,在教育界引起了軒然大波。

7月25日,北京大學發布公告,宣布自2025年秋季學期起,實施一系列優化本科學生學業評價的重大改革措施。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舉措是,自2025級本科新生起,學生學業評價將全面取消績點(GPA ,即grade point average)排名,成績單將作為學業情況的完整體現。
對于這次改革,北大學生的反響不一。有人為此鼓掌叫好,感嘆“早生了幾年”;也有人表示,自己喜歡卷績點,只因為這是沒有背景、沒有家世的普通人的唯一出路。
績點伴隨著每個大學生走過大學四年。比別人更高的績點,意味著優先級更高的保研名額,意味著綜測評定中更靠前的排名。在這樣的考核機制下,知識似乎變成了副產物,而績點才是學生追求的結果。
大學生與績點的愛恨糾葛從何而來?取消績點究竟會避免內卷,還是換成另一種方式內卷?
“沒有績點的大學不完整”
如今在大學里普遍實行的績點制,一直以來伴隨著不少批評的聲音,“會加劇高分低能”可能是其中聲量最大的一條。
“在如今的校園里,學生普遍以低質量功課換取老師的高評分。”威廉·德雷謝維奇在《優秀的綿羊》一書中,曾談到美國大學中成績膨脹、分數虛高帶來的問題。他指出,這是因為“平均GPA越高,分數貶值越厲害,用分數區分學生之間的素質差異也就變得更加困難”。盡管如此,績點自出現以來就作為評價學生成績的重要的標準,并長期存在。
績點的歷史可以追溯至19世紀末的美國。1894年,哈佛大學率先使用學分制;到了20世紀初,美國各個高校也逐漸推行。績點制度也是從那時誕生,之后被多國沿用至今。
20世紀90年代后,我國的高校陸續進行學分制改革,績點制作為學分制的配套機制,成為高校評價學生學習狀態和成果的重要考核標準。
一門課的成績越高,最后的平均績點(GPA)也就越高。有大學生在社交媒體上分享績點在大學中占的權重之大:“評選各種榮譽稱號,例如優秀學生干部、優秀共青團員,或申請國家獎學金的時候,績點的參考占比達到80%。”可以說,績點是大學中最重要的一條游戲規則。
目前主流的績點計算方式主要有五分制和四分制,都和學生每門課程的成績緊緊掛鉤。直觀的數字表達和評價標準,像一把通用的標尺,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不同學科、不同學校的學生進行評獎、升學、應聘時的橫向對比。
但另一方面,也有聲音認為,績點制讓學生落入分數至上的窠臼。學生為了獲得更高的績點,樂于選擇給分更寬松、更高的“水課”,可能放棄對知識結構有用的課程,減少了實踐時間。
實際上,早在2015年,清華大學就率先以12檔等級制取代GPA評價,強調多元評價體系,復旦大學等知名院校,近幾年也均對績點機制進行過改革嘗試,目的都是破除“唯分數論”,讓學生不再為了績點而卷績點。
不少人悲觀地認為,即使沒有了績點這個標準,仍然會有其他評價機制代替績點,只是內卷的內容和方向發生了變化,內卷的動作不會改變。取消績點,就可以避免教育的內卷嗎?這個答案仍然不得而知。
北大學生,也逃不過水課
Aria剛剛在北京大學度過第一年大學時光。作為第一批改革群體中的一員,北大關于績點的變化,將會在她身上有著持續的影響。
整個大一,Aria都對績點非常在意。為了拿高分,她選過自己不太感興趣,但聽說給分比較寬裕的課程。選課時,這類給分高的“水課”都會爆滿。但出乎意料的是,盡管Aria是沖著給分高選了這門課,最后這門課程反倒是她整個學期分數最低的學科。Aria把原因歸結為“自己實在沒有興趣”。
目前排在專業第一名的Aria,屬于對此次北大改革叫好的一批人。
Aria觀察到,在一個全員普遍優秀的環境里,很多人都試圖通過提高零點幾分的績點來縮小和他人的差距,提高自身排名。在她看來,這種內卷是無益的。“為了獲得零點幾分的優勢,可能要投入大量精力去內卷,其實就是一個邊際效益遞減的現象。”
取消績點的爭議,集中在是否會影響保研或留學,以及能否真正解決學生內卷等方面。但放在北京大學的背景下,這些擔憂似乎顯得有些多余。
“只要在北大不是特別擺爛,大概率都可以拿到推免名額。”在Aria看來,取消績點對于北大學生保研的影響并不大。她隱晦地提到,對于目標院校來說,光是本科來自北京大學這一點,就會讓申請的學生自帶很高的認可度。
從2025年全國部分院校保研推免率來看,39所985院校的平均保研率為28.6%,其中北京大學以65.07%的保研率居全國首位(1954人),而在一些雙非院校,每年可能只有不到5%的學生能獲得保研名額。
因此,北大取消學分績點的舉措,更像是本身就擁有足夠優質教學資源的高校,在探索減輕學生負擔方面的錦上添花。
除了取消績點外,北大此次改革還推出PF制。不同于以往給出具體的分數,學生每年可以選擇一門課程,不記具體成績,只有“通過”和“不通過”兩種評定結果。
即將大四的北大學生孟菲認為,過去一些自己感興趣又因焦慮成績而放棄的課程,現在因為有了這個政策,就可以放心去選擇。
但對于績點制度改革本身,孟菲則持觀望態度。在她看來,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無論有沒有績點,都會有一個評價體系去評估成績情況。如果想要獲得競爭激烈的項目,該卷的還是要卷。“績點改革只是說取消了一個量化的標準,讓大家平時不用特意盯著這個數字,給大家心理上起到一個稍微放松一點的作用吧。”
當被問及今后選課的標準時,Aria表示,雖然還是秉承興趣優先的原則,但仍然要考慮給分情況。“如果給分情況不好,我是一定不會去選的。”
取消績點,其他大學能跟上嗎?
作為教育改革的先鋒,北京大學走在了國內大學的前列。而對于其他高校而言,績點可能更是一個既讓他們感到焦慮,又無法徹底割舍的存在。
馬上要大四的林徹,就讀于一所華南地區的211院校。這個暑假,他剛剛結束清華大學的夏令營項目。雖然對方聲稱,此次只是體驗式項目,但想要保研的林徹還是非常看重這次機會。和北京大學學生面臨的環境不同,林徹所在的專業,每年可能只有前10%的人能拿到推免資格。
步入大學的時候,林徹其實對于績點的重要性沒什么概念。后來,一個本專業的學長告訴他,大一有兩門課程比較難,如果學好了,可以拉開和其他人的分數差距,他才花了不少心思在這兩門課上。學期結束,果然收獲了不錯的績點。
從這時開始,林徹意識到了績點的重要性,主動放棄一些給分相對嚴格的課程。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說,自己選的所有選修課,基本上都是沖著能拿高分才選的,比如觀賞魚養殖、音樂欣賞、中醫知識這些課程,實際上,他對于這些學科興趣不大。對林徹來說,每天坐在教室里聽一些含金量不高的知識,像一種煎熬,但為了績點,也只能堅持下來。
與此同時,林徹也發現,身邊想要保研或出國留學的同學,都開始加入到“卷”績點的行列。為了提高績點,班上同學會搶著去擔任某一門課程的課代表,還會超額完成老師布置的非強制性的學習任務。林徹記得,在一門專業課上,只要上課回答四次問題,就可以拿到滿分的平時分,但還是有一位同學,回答了超過十次問題。
林徹也不可避免地投身到內卷的浪潮中。寫一門課程論文的時候,老師對字數的要求是3000字。為了看上去更用心,林徹把論文的主體拆分成了好幾個部分,最后寫到了2萬字。
在林徹看來,北京大學的學生可能并不需要績點來證明自己的實力。林徹有一個考上北大研究生的朋友,研究生三年時間沒有參加實習,沒有發表學術論文,也沒有參加任何比賽,但畢業后直接入職了一個快消品大廠。“但對于學歷認可度沒有那么高的大學生來說,可能還是需要一些分數來證明自己。”
雖然有些反感應付考試來獲得高分績點,但林徹還是認為,無論學校是否取消績點,都會存在排序的需求。“取消了績點,依然會有千千萬萬個評價標準。在這個體系中,仍然需要一個東西去證明人的優秀程度。也因為這一點,內卷的趨勢很難遏制。”
“雖然取消績點可能是一個治標不治本的事情,但我還是希望我們學校可以效仿一下北大。因為比起坐在教室里卷績點,我還是寧愿去參加比賽和實習。”他最后補充道。
沒有升學打算的學生,對于績點則有不同的看法。明年要從一所語言類雙非院校畢業的劉璐,不考慮保研和留學,打算直接參加工作。她的觀點和林徹完全不同。在她看來,有績點反而是一套更優的標準。
看到北大取消績點的新聞,劉璐覺得這只是一個少有的個例。“可能對于那些非常自律、目標清晰的學生來說,績點是個負擔。但對她來說,有績點反而能令她產生認真對待學業的動力,因此績點更像是大學生活的一個方向和目標,不至于日后回想起來,覺得自己渾渾噩噩地度過了大學四年。
但劉璐愿意為績點付出的努力并非無止境的。提到自己有個想要保研的師姐,會因為老師某一次作業打分稍微低了一點而去理論,劉璐坦言,自己不會像這位師姐一樣,如此嚴肅認真地追求完美績點。她打算畢業后直接工作,對她來說,目前3.7分左右的績點已經夠用了,“我并不會很卷績點,我只是覺得需要績點來反饋我某一個階段的學習成果。”
“其實,我有點想象不出來,如果一個學校不靠績點作為評價標準的話,它可以靠什么去評判呢?”劉璐問道。